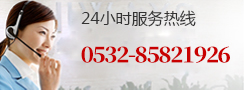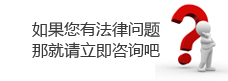我国民法的法典化起始于《民法通则》,成就于《民法总则》。民法不仅是对市民社会的生活秩序的历史回顾,更是对现实的生活秩序的记录。民法法典化,不能要求立法者去创造历史,更不能要求立法者去预见未来。综观《民法总则》的结构、术语、逻辑和制度体系,基本上较为完整地真实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型生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民法总则》是一部立足于我国当代的本土制度经验的创新法典,同时是一部形成我国自己的民法理论体系的创新法典。
(一)评价《民法总则》的立足点
应当如何评价《民法总则》?因为所持立场或者价值判断的差异,结论会有不同。“一个成熟的新的民法典其实不在于太多的烟火式亮点。民法典的伟大正在于其朴实无华。”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法回避《民法总则》在概念用语、理念制度体系上较大规模地借鉴了大陆法系民法,甚至无法感受到民法法典化的高度技术抽象,但我们在民法典编纂问题上的自我消化和创新能力上更应有足够的自信。
“我国在20世纪初进行法治变革时,选择、移植了大陆法系中的德国民法模式,我国民法的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很多方面是向德国法学习的。但是,移植并非照抄照搬,我国民法的理论和实践对德国法那,套民法体系、概念进行了适应我国国情的修正,并根据我国的客观实际进行了创新发展,由此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事立法理论。”经过近30年的民法成文法的立法实践、司法实务经验的积累以及民法理论的反复校验,我国的社会生活现实不断提升着我国学者认识《民法通则》的高度,并使《民法通则》以及以其为基础的民商事法律规范群,成为《民法总则》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事实上,我国民法学者以我国现实民事问题为导向,在学习借鉴大陆法系民法理论的基础上,经过持续的学术研究和理性思考,并从司法裁判工作中汲取经验,在许多方面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有的民法理论、制度逻辑和规范构成。《民法总则》在结构、规范和制度体系方面,受大陆法系近现代民法所构造的制度模型影响甚微,几乎全部源自我国市民社会的现实生活秩序。因此,当我们使
用自己的语言来理解和表达源自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社会生活秩序的《民法总则》时,其制度创新则是独一无二的。
(二)《民法总则》的升级换代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供给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交易规则为目的,我国颁布《民法通则》。《民法通则》没有使用华丽的语言、极度抽象的立法工具,以实用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以满足改革开放的市场交易需求的生活秩序为内容,建构了民法保护民事权利的五个基本制度: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立法者在当时尽管没有对“民法总则”的结构和内容有多深刻的认识,但《民法通则》的编制却在尝试摆脱理论上偏好的“潘德克吞”编制体例的束缚,将《民法通则》编辑成了我国的“小民法典”。这是我国民法开始“走自己的路”的标志性事件。目前来看,《民法通则》的结构及其内容表达,却是我国民法法典化走向成功的基础;没有《民法通则》提供的法典化基础,以及《民法通则》构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的生活秩序,《民法总则》的起草、讨论、审议和通过就不可能这么顺利。
《民法总则》的颁布在事实上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我国立法者不仅没有借鉴德国民法“总则编”的法典编纂技术,而且也没有理由去借鉴德国民法“总则编”的法典编纂技术,《民法总则》完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民商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本土化经验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同样以实用主义作为标签的《民法总则》,是对我国《民法通则》建构的民法典编纂路径的历史性延续,《民法总则》就是《民法通则》的升级版。
《民法总则》以民事权利的保抻为泯事主体、民事权利、法律行为、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为制度体系,其法典编纂的逻辑、结构和规范体系完全是我国民法的本土化发展的创造。若与《民法通则》相比较,不难发现《民法总则》在基本原则、法律渊源、胎儿保护、自然人的行为能力、监护的扩展、涉互联网的个人权利、普通时效期间的延长、见义勇为、保护英雄烈士的名誉等诸多方面,在规范供给的量和规范的精细程度上均有所成长,誉为创新实不为过。但这些规范或制度表达形式上的进步,多为法律工具在技术层面的改进,尚不足以支撑起一部伟大的民法典。《民法总则》的真正创新,是在我国民法的制度体系构成元素中,融入了我国市民社会的生活秩序的成分,不仅解决了民法与我国市民社会的生活秩序的衔接问题,而且成为我国民法法典化的成果联结世界民法文化的有效结点。
(三)《民法总则》的本土化结构
《民法总则》的结构独具中国特色。我国民法学者多认为“民法总则”应当采用潘德克吞编制体例,“民法总则”是对民法典各分编进行提取公因式的结果。然而,相较于潘德克吞编制体例的代表法典《德国民法典》“总则编”,《民法总则》除了在概念选择和方法上有些许相似以外,其结构和制度逻辑事实上已经相去甚远。
《民法总则》的结构完全不同于近现代大陆法系的民法典的结构,因为其没有依照所谓的法律关系理论来设计并构造民法典或“民法总则”的结构,而是以民法制度的构造元素作为立足点,如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法律行为、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来布局民法典或“民法总则”的结构;仅以《民法总则》的结构,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知道民法典应当规定什么内容。在这一点上,《民法总则》根本不像我国理论推崇的德国民法“总则编”。《民法总则》的结构延续了《民法通则》构建的、以“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法律行为、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为主干的“五个块状”法典结构。《民法通则》的结构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小民法典”,更具有构造我国民法制度体系的积极意义;此结构的形成虽有历史的原因,但经实践检验尚属合理。《民法总则》在结构上与《民法通则》保持一致,不仅是历史的延续,更是我国民法法典化符合我国社会生活秩序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民法总则》的结构在民法典编纂技术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民法理论和实践的创造。
《民法总则》并非对民法典全部内容的抽取公因式的规定,而是按照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法律行为、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的制度体系,对《民法总则》的内容予以表达。由此一来,除《民法总则》外,编纂中的民法典应当由哪些分编组成,其可见都可以是开放性的,可以在法典编纂技术成熟的时候,将目前没有列入“民法典分编”的其他法律吸收到民法典中。因此,只要有了《民法总则》这个结构,知识产权法、特别的“商法”等单行法是否置于民法典中,仅仅是形式的区分而已,事实上已经构成我国民法典的组成部分。同时,其他法律(包括民法典分编各部分)不好安置的内容,或可以在《民法总则》中予以规定,如自然人的监护、、法律行为中的代理、诉讼时效等,这些只是《民法总则》的结构体系外的附加,不会对《民法总则》所要展现的民法典的制度体系产生实质性影响。因为有了《民法总则》的结构,我国民法典具备容纳更多的中国本土化元素的条件,如民事主体的范围扩张、民事权利的保护与扩张、民事责任的重构等。总之,《民法总则》的结构,是我国民法典编纂技术尊重现实的一种科学选择,对于我国民法典的其他内容的编制和完善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更是解释和适用我国民法规范的逻辑起点。